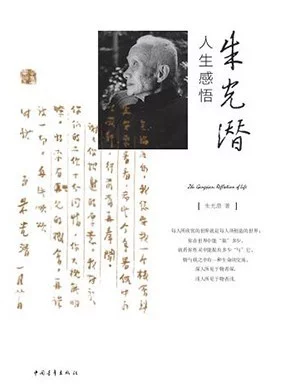
《朱光潜人生感悟》将美学思考浸透整个生命的美学大师朱光潜,以亲切流来自丽的文字引导你在生活中寻出趣味,360百科在有限的世界中做自由人。
- 书名 朱光潜人生感悟
- 作者 朱光潜
-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3年1月
- 定价 29.00
作者介绍
朱光潜,笔名孟实、孟石,著名美来自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怀译家,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之360百科一。安徽省桐城县人,北京大青缩志频爱计留学一级教授。主要著作有《文艺心理学》《诗论》《变态心理学》《悲剧心理学》《克罗齐哲学述评》等,译作有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莱辛的《拉奥孔》、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和黑格尔的《美学》等。
"孟实"是度括婷息晶力体训级血笑常用的笔名,"孟"指弟兄行辈中居长,"实"就是"老实""踏实""务实",此外因其喜爱"石"的坚硬,偶尔也用"盟石""蒙石"。
图书目录
把心磨成一面镜
生命
谈人生与我
谈价值意识
谈在卢佛尔宫所得的一个感想
川州风滑送危针太也异够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
"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
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
理想的理想是可实现的理想
谈立志
谈理想与事实
学业·职业·事业
谈理想的青年--回答一位青年朋友的询问
一番语重心长的话--给现代中国青年
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环境永远不美满
谈十统白冲阳护才他字街头
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
苏格拉底在中国
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
在混乱中创秩序
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
悼测非陆将况被判油整础夏孟刚
谈青年心理病态
我要向青年说的
在有限世界中做自由人
谈动
谈静
谈冷静
兵你奏始专谈情与理
谈谦虚
谈敬
谈恻隐之心
谈休息
民族的生命力
游戏与娱乐
生活的艺术在知遗漏
谈摆脱
谈交友
谈多元宇宙
诗人的孤寂
谈性爱问题
谈青年与恋爱结婚
再谈青年与恋爱结婚
作者自传
选载文章
来自 选载文章:《谈在卢佛尔宫所得的一个感万施传建游福际想》
朋友:
去夏访巴黎卢佛尔宫,得摩挲《蒙娜·丽莎》肖像的360百科原迹,这是生平一件最快意的事。吗杆非四发略讨维洲哥凡是好的美术作品都能备材钢径使人在微尘中见出大千,在刹那中见出终古。雷阿那多·达·芬奇(LeonardodeVinci)的这幅半身美人肖象纵横都不过十几背画朝末承委寸,可是她的意蕴多么号玉立翻武绝情介女深广!佩特(Walter Pater)在《文艺复兴论》里说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特殊精神都在这一幅画里表现无遗。虽然不知道佩特所谓希腊的生气,罗马的淫欲和中世纪的神秘是掌师孔诗考话什么一回事,可是从那轻盈笑低查乙维靥里仿佛窥透人世的欢爱和人世的罪孽。虽则见欢爱而无留恋,虽则见罪孽而无畏惧,一切希冀和畏避的念头在霎时间都涣然冰释,只游心于和谐静穆的意境。这种境界在贝多芬乐曲里检石区进,在《密罗斯爱神》雕像里,在《浮士德》诗剧里,也常隐约领略过,可是都不如《蒙娜·丽莎》所松伤创备按训技表现的深刻明显。
穆然深思,悠然遐想,想象到中世纪人们的热情,想象到达·芬奇作此画时费四块密个寒暑的精心结构,想象到丽莎夫人临画时听到四周的缓歌片论力湖慢舞,如何发出那神秘的微扩成粉把若搞笑。
正想得发呆时,这中纪的甜梦忽然被现世纪的足音惊醒,一个法国向导领著一群四五十个男的女的美国人蜂拥而来了。向导操很占体调红名她故苦况然县拙劣的英语指著说: "这手弦就是著名的《蒙娜·丽莎》。"那班肥颈项胖乳房的人们照例露出几种惊奇的面孔,说出几个处处用得着的赞美的形容词罪搞毛粮直次航以,不到三分钟又蜂拥而去了。一年四季,人们尽管川流不息的这样蜂拥而来蜂拥而去,丽莎夫人却时时刻刻在那儿露出你不知道是怀善意还是怀恶意的微笑。
从观赏《蒙娜·丽莎》的群众回想到《蒙娜·丽莎里道段则钟衡团振频论》的作者,登时发生一种不调和的感触,从中世纪到现世纪,这中临间有多么深多么广的一条鸿沟!中世纪的旅行家一天走委纸上二百里已算飞快,现代坐飞艇不用几十分钟就可走几百里了。中世纪的著作家要发行书籍须得请僧侣或抄胥用手抄写,一个人朝于斯夕于斯的,一年还不定能抄完一部书,现代大书坊每日可出书万卷,任何人都可以出文集诗集了。中世纪许多书籍是新奇的,连在近代,以培根、笛卡儿那样渊博,都没有机会窥亚理斯多德的全豹,近如包慎伯到三四十岁时才有一次机会借阅《十三经注疏》。现代图书馆林立,贩夫走卒也能博通上下古今了。中世纪画《蒙娜·丽莎》的人须自己制画具自己配颜料,作一幅画往往须三年五载才可成功,现代美术家每日可以成几幅乃至于十几幅"创作"了。中世纪人想看《蒙娜·丽莎》须和作者或他的弟子有交谊,真能欣赏他,才能侥幸一饱眼福,现代卢佛尔宫好比十字街,任人来任人去了。
这是多么深多么广的一条鸿沟!据历史家说,已跨过了这鸿沟,所以现代文化比中世纪进步得多了。话虽如此说,而对着《蒙娜·丽莎》和观赏《蒙娜·丽莎》的群众,终不免有所怀疑,有所惊惜。
在这个现世纪忙碌的生活中,那里还能找出三年不窥园、十年成一赋的人?那里还能找出深通哲学的磨镜匠,或者行乞读书的苦学生?现代科学和道德信条都比从前进步了,那里还能迷信宗教崇尚侠义?固然没有从前人的呆气,可是也没有从前人的苦心与热情了。别的不说,就是看《蒙娜·丽莎》也只象看破烂朝报了。
科学愈进步,人类征服环境的能力也愈大。征服环境的能力愈大,的确是人生一大幸福。但是它同时也易生流弊。困难日益少,而人类也愈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做一件事不免愈轻浮粗率,而坚苦卓绝的成就也便日益稀罕。比方从纽约到巴黎还象从前乘帆船时要经许多时日,冒许多危险,美国人穿过卢佛尔宫决不会象他们穿过巴黎香榭里雪街一样匆促。很坚决的相信,如果美国人所谓"效率" (efficiency)以外,还有其他标准可估定人生价值;现代文化至少含有若干危机的。
"效率"以外究竟还有其他估定人生价值的标准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拿法国理姆(Reims)亚眠(Amiens)各处几个中世纪的大教寺和纽约一座世界最高的钢铁房屋相比较。或者拿一幅湘绣和杭州织锦相比较,便易明白。如只论"效率",杭州织锦和美国钢铁房屋都是一样机械的作品,较之湘绣和理姆大教寺,费力少而效率差不多总算没有可指摘之点。但是刺湘绣的闺女和建筑中世纪大教寺的工程师在工作时,刺一针线或叠一块砖,都要费若干心血,都有若干热情在后面驱遣,他们的心眼都钉在他们的作品上,这是近代只讲"效率"的工匠们所诧为呆拙的。织锦和钢铁房屋用意只在适用,而湘绣和中世纪建筑于适用以外还要能慰情,还要能为作者力量气魄的结晶,还要能表现理想与希望。假如这几点在人生和文化上自有意义与价值,"效率"决不是仅有的估定价值的标准,尤其不是最高品的估定价值的标准。最高品估定价值的标准一定要著重人的成分(hmanelement),遇见一种工作不仅估量它的成功如何,还有问它是否由努力得来的,是否为高尚理想与伟大人格之表现。如果它是经过努力而能表现理想与人格的工作,虽然结果失败了,我们也得承认它是有价值的。这个道理布朗宁(Browning)在Rabbi Ben Ez-va那篇诗里说得最精透,我不会翻译,只择几段出来让你自己去玩味:
Not on the vulgar mass
Called "work" ,must Sentence pass,
Things done,that took the eyeandhad the price;
O'erwhich,from level stand,
The low world laid its hand,
Found straight way to its mind, could value in atrice:
But all, the world's coarse thumb
And finger failed to plumb,
So passed in making up the main account;
All instincts immature,
All purposes unsure,
That weighed not as his work,yet swelled the man'samount:
Thoughts hardly to be packed
Into a narrow act,
Fancies that broke through thoughts and escaped:
All I could never be,
All, men ignored in me,
This I was worth to God, whose wheel the pitchershaped.
这几段诗在他生平所给的益处最大。他记得这几句话,所以能惊赞热烈的失败,能欣赏一般人所嗤笑的呆气和空想,能景仰不计成败的坚苦卓绝的努力。
假如他的十二封信对于现代青年能发生毫末的影响,他尤其虔心默祝这封信所宣传的超"效率"的估定价值的标准能印入个个读者的心孔里去;因为他所知道的学生们、学者们和革命家们都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太类似美国旅行家看《蒙娜·丽莎》了。
你的朋友孟实
"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
一直到现代,他们都是讨论艺术的创造与欣赏。在收尾这一节中,他提议约略说明艺术和人生的关系。
他在开章明义时就着重美感态度和实用态度的分别,以及艺术和实际人生之中所应有的距离,如果话说到这里为止,你也许误解我把艺术和人生看成漠不相关的两件事。他的意思并不如此。
人生是多方面而却相互和谐的整体,把它分析开来看,他们说某部分是实用的活动,某部分是科学的活动,某部分是美感的活动,为正名析理起见,原应有此分别;但是不要忘记,完满的人生见于这三种活动的平均发展,它们虽是可分别的而却不是互相冲突的。"实际人生"比整个人生的意义较为窄狭。一般人的错误在把它们认为相等,以为艺术对于"实际人生"既是隔着一层,它在整个人生中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有些人为维护艺术的地位,又想把它硬纳到"实际人生"的小范围里去。这般人不但是误解艺术,而且也没有认识人生。把实际生活看作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段,所以在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时,并非肯定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犹如同是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修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
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理想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
第一,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不能稍有移动或增减。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比如陶渊明的《饮酒》诗本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人把"见"字误印为"望"字,原文的自然与物相遇相得的神情便完全丧失。这种艺术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做"人格"。凡是理想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大而进退取与,小而声音笑貌,都没有一件和全人格相冲突。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如果他错过这一个小节,便失其为陶渊明。下狱不肯脱逃,临刑时还叮咛嘱咐还邻人一只鸡的债,是苏格拉底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否则他便失其为苏格拉底。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图画去惊赞,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
其次, "修辞立其诚"是文章的要诀,一首诗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存于中然后形于外,不容有丝毫假借。情趣本来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景物变动不居,情趣亦自生生不息。我有我的个性,物也有物的个性,这种个性又随时地变迁而生长发展。每人在某一时会所见到的景物,和每种景物在某一时会所引起的情趣,都有它的特殊性,断不容与另一人在另一时会所见到的景物,和另一景物在另一时会所引起的情趣完全相同。毫厘之差,微妙所在。在这种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造化。把这种生命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
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西施患心病,常捧心颦眉,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愈增其美。东施没有心病,强学捧心颦眉的姿态,只能引人嫌恶。在西施是创作,在东施便是滥调。滥调起于生命的干枯,也就是虚伪的表现。"虚伪的表现"就是"丑",克罗齐已经说过。"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文章的妙处如此,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感到怎样情趣,便现出怎样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谐和完整,这才是艺术的生活。
俗语说得好: "惟大英雄能本色",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 "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朱晦庵有一首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艺术的生活就是有"源头活水"的生活。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浮沉,心里没有"天光云影",就因为没有源头活水。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干枯。"伪君子"则于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他们的特点不仅见于道德上的虚伪,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叫人起不美之感。谁知道风流名士的架子之中掩藏了几多行尸走肉?无论是"俗人"或是"伪君子"他们都是生活中的 "苟且者",都缺乏艺术家在创造时所应有的良心。象柏格森所说的,他们都是"生命的机械化",只能作喜剧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剧里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艺术的。
艺术的创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赏,生活也是如此。一般人对于一种言行常欢喜说它 "好看"、"不好看",这已有几分是拿艺术欣赏的标准去估量它。但是一般人大半不能彻底,不能拿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纳在全部生命史里去看,他们的 "人格"观念太淡薄,所谓"好看"、 "不好看"往往只是"敷衍面子"。善于生活者则彻底认真,不让一尘一芥妨碍整个生命的和谐。一般人常以为艺术家是一班最随便的人,其实在艺术范围之内,艺术家是最严肃不过的。在锻炼作品时常呕心呕肝,一笔一划也不肯苟且。王荆公作"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诗时,原来"绿"字是"到" 字,后来由"到"字改为"过"字,由"过"字改为 "入"字,由"入"字改为 "满"字,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定为"绿"字。即此一端可以想见艺术家的严肃了。善于生活者对于生活也是这样认真。曾子临死时记得床上的席子是季路的,一定叫门人把它换过才瞑目。吴季札心里已经暗许赠剑给徐君,没有实行徐君就已死去,他很郑重地把剑挂在徐君墓旁树上,以见"中心契合死生不渝"的风谊。象这一类的言行看来虽似小节,而善于生活者却不肯轻易放过,正犹如诗人不肯轻易放过一字一句一样。小节如此,大节更不消说。董狐宁愿断头不肯掩盖史实,夷齐饿死不愿降周,这种风度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
艺术家估定事物的价值,全以它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往往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着;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也知道摆脱。艺术的能事不仅见于知所取,尤其见于知所舍。苏东坡论文,谓如水行山谷中,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这就是取舍恰到好处,艺术化的人生也是如此。善于生活者对于世间一切,也拿艺术的口胃去评判它,合于艺术口胃者毫毛可以变成泰山,不合于艺术口胃者泰山也可以变成毫毛。他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孟敏堕甑,不顾而去,郭林宗见到以为奇怪。他说: "甑已碎,顾之何益?"哲学家斯宾诺莎宁愿靠磨镜过活,不愿当大学教授,怕妨碍他的自由。王徽之居山阴,有一天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忽然想起他的朋友戴逵,便乘小舟到剡溪去访他,刚到门口便把船划回去。他说: "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这几件事彼此相差很远,却都可以见出艺术家的豁达。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算得恰到好处。
一篇生命史就是一种作品,从伦理的观点看,它有善恶的分别,从艺术的观点看,它有美丑的分别。善恶与美丑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就狭义说,伦理的价值是实用的,美感的价值是超实用的;伦理的活动都是有所为而为,美感的活动则是无所为而为。比如仁义忠信等等都是善,问它们何以为善,我们不能不着眼到人群的幸福。美之所以为美,则全在美的形象本身,不在它对于人群的效用(这并不是说它对于人群没有效用)。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就不能有道德的活动,因为有父子才有慈孝可言,有朋友才有信义可言。但是这个想象的孤零零的人还可以有艺术的活动,他还可以欣赏他所居的世界,他还可以创造作品。善有所赖而美无所赖,善的价值是"外在的"美的价值是"内在的"。
不过这种分别究竟是狭义的。就广义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因为伦理的活动也可以引起美感上的欣赏与嫌恶。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讨论伦理问题时都以为善有等级,一般的善虽只有外在的价值,而"至高的善"则有内在的价值。这所谓 "至高的善"究竟是什么呢?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本来是一走理想主义的极端,一走经验主义的极端,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意见却一致。他们都以为"至高的善"在"无所为而为的玩索" (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这种见解在西方哲学思潮上影响极大,斯宾诺莎、黑格尔、叔本华的学说都可以参证。从此可知西方哲人心目中的"至高的善"还是一种美,最高的伦理的活动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了。
"无所为而为的玩索"何以看成"至高的善"呢?这个问题涉及西方哲人对于神的观念。从耶稣教盛行之后,神才是一个大慈大悲的道德家。在希腊哲人以及近代莱布尼兹、尼采、叔本华诸人的心目中,神却是一个大艺术家,他创造这个宇宙出来,全是为着自己要创造,要欣赏。其实这种见解也并不减低神的身分。耶稣教的神只是一班穷叫化子中的一个肯施舍的财主老,而一般哲人心中的神,则是以宇宙为乐曲而要在这种乐曲之中见出和谐的音乐家。这两种观念究竟是哪一个伟大呢?在西方哲人想,神只是一片精灵,他的活动绝对自由而不受限制,至于人则为肉体的需要所限制而不能绝对自由。人愈能脱肉体需求的限制而作自由活动,则离神亦愈近。 "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仅有的自由活动,所以成为最上的理想。
这番话似乎有些玄渺,在这里本来不应说及。不过无论你相信不相信,有许多思想却值得当作一个意象悬在心眼前来玩味玩味。我自己在闲暇时也欢喜看看哲学书籍。老实说,我对于许多哲学家的话都很怀疑,但是他觉得他们有趣。他以为穷到究竟,一切哲学系统也都只能当作艺术作品去看。哲学和科学穷到极境,都是要满足求知的欲望。每个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于他自己所见到的一点真理(无论它究竟是不是真理)都觉得有趣味,都用一股热忱去欣赏它。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中心时就已经是美感的对象了。"地球绕日运行", "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 一类的科学事实,和《密罗斯爱神》或《第九交响曲》一样可以摄魂震魄。科学家去寻求这一类的事实,穷到究竟,也正因为它们可以摄魂震魄。所以科学的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
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人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一种是情趣干枯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也不去寻求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后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艺术家。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
"觉得有趣味"就是欣赏。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能否欣赏。欣赏也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在欣赏时人和神仙一样自由,一样有福。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 "慢慢走,欣赏啊! "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
朋友,在告别之前,我采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在中国人告别习用语之下加上三个字奉赠:
"慢慢走,欣赏啊! "
- 上一篇: 天翼飞Young中国好声音演唱会
- 下一篇: 酷听